你能想象一份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吗?在我们经常喝的啤酒——雪花啤酒背后有这样一位一直坚持啤酒酿造的酿酒匠人,他把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他是中国第一批到德国学习啤酒酿造技术和质量管理的人才;凭借一份致力于将中国本土精酿味道带到全世界的工匠精神,他跟啤酒打了近30年交道,光是啤酒的苦味,研究了20年……他是桂城匠人,雪花啤酒副总经理、酿酒专家骆怀民。
国内首批赴德学习啤酒酿造技术人才
80年代初能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时的骆怀民学的是发酵工程专业。“最开始我以为是做馒头面包的,没想到是研究酵母等微生物的。”骆怀民笑着说,没想到跟酵母打了一辈子交道。
作为科班出身的骆怀民,年轻时曾被派到德国学习啤酒酿造技术和质量管理。
“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制造的精良,但那个年代要出国学习深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到德国,骆怀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职业精神。严谨的德国对传统产业的要求十分精细,要成为一名专业酿酒师,需要经历三年枯燥重复的基础工作之后才能进入大学获得成为专业酿酒师的资格。
骆怀民说,德国人很“专一”,特别是对岗位的要求,选择了一个职业或岗位后,会一直做到底,一旦换岗了,必须经过系统严格的学习和培训。“这种职业精神和‘专一’让德国人的产品质量能保证稳定,从每个细节抓起。”骆怀民说。正如作为一名酿酒师,从上游的一粒大麦、一颗酒花、一滴水,到下游的物流、售卖,都要关注。
花了4年摸清微生物脾性
啤酒,是以大麦为原料,啤酒花为香料,经过麦芽糖化和啤酒酵母酒精发酵制成。其中的酵母就是里面最神秘的东西。这个直径不足百分之一毫米的微生物,虽然只有用显微镜才能一窥真容,但它却能赋予每种啤酒与众不同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所以把酵母誉为啤酒的灵魂一点都不为过。
“通常1毫升酵母原菌种,经过20天左右的扩大培养,复制出来的酵母菌,足够生产300千升、约60万瓶啤酒,可谓是真正的‘四两拨千斤’。”骆怀民说。
作为一名优秀的酿酒师,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摸清这群微生物的脾性,好生伺候,从“喂养”酵母的麦汁,到酵母生活环境的温度、压力、含氧量,甚至是生产车间的环境卫生等种种指标一样都不能马虎。
酿酒用的大米必须是脱壳3天之内的新鲜米,酿造用水每隔2小时就得品尝一次,一个酒瓶子要洗几十分钟才算合格,走酒的管道是用啤酒“刷”干净的,煮过瓶盖垫片和刷瓶的水都要用嘴品评把关,生产所用的压缩空气要进行细菌检测……不要以为这是哪个微生物研究所,或是哪个精密仪器实验室,其实这就是雪花啤酒一个普通的生产车间。
研究啤酒“苦味”长达20年
鉴别啤酒的好坏,讲究 “一看,二闻,三尝”。好啤酒看起来,泡沫丰富、洁白细腻,轻轻摇晃后挂杯持久,酒色清亮宛如琥珀;再说闻,只要把啤酒杯端起,深吸一口,优质啤酒会散发浓浓的麦香,且略带苦味的啤酒花香;最后尝酒时,抿一小口啤酒,让酒精在口腔内停留和转动一下再咽下去,感受二氧化碳的刺激和酒体的柔和、醇厚。
经常有身边的朋友问骆怀民:“好啤酒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阶段上,他有着不同的答案。
从在一个地方工作,到在全国不同的区域工作;从恪守自己企业独特的典型风味,到尊重各地消费者不同的口味特征,骆怀民心目中好啤酒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他心中的“品质内涵”,开始由过去的“专家标准”,转向了“消费者标准”。
在愈加年轻化、个性化的今天,消费者的口味也越来越挑剔,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已经不能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了,对于酿酒师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动脑子,研发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
“从刚开始的22到后来的20~16,再到1995年前后的15,到2000年的10,再到2016年的8。”光是这个苦味,骆怀民和团队就用了20年研究。
作为一名普通的酿酒师,骆怀民是一瓶啤酒背后的幕后人物。他已记不清有多少瓶啤酒经我之手被送往世界各地,但当大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畅饮来自中国的啤酒时,那份骄傲和快乐就是对酿酒师最好的回报,这也是对中国品质、品牌的最大认可。
以上就是关于骆怀民:20年的雪花啤,一直在坚持的内容,让我们为这位具有执着精神的酿酒匠人给予掌声!


 注册
注册
 登录
登录

 导航
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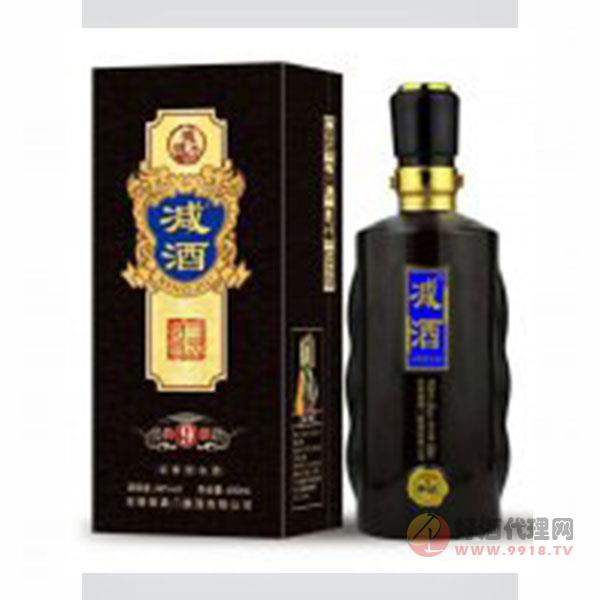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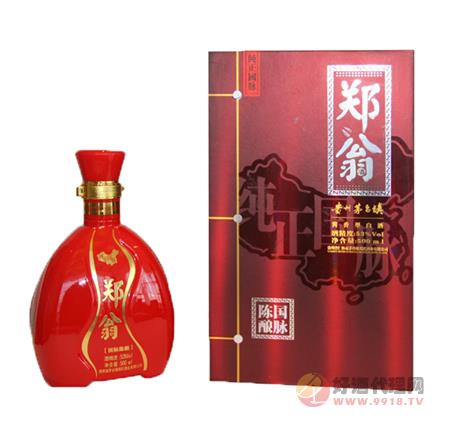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3-2025
Copyright © 2013-2025